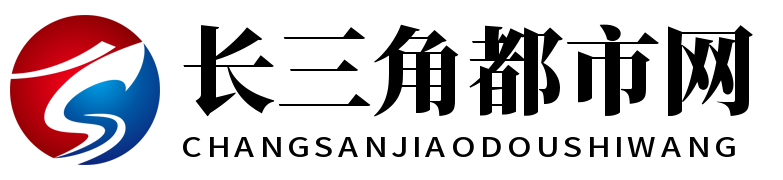问:作为一位长期扎根曲靖的原创音乐人,您是在何种契机下创作《阿诗玛的情话》的?
关兴瞳: 是今年夏天在上海的一个夜晚。我结束工作后,独自走在黄埔江边。江风温润,霓虹璀璨,这座城市的夜色有一种繁华深处的静。就在这时,我毫无预兆地想起——阿诗玛杨丽坤,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二十五年了。
那一刻的感觉非常奇特,我站在她生命终点所在的江边,思绪却瞬间穿越千里,回到了她艺术生命起点的云南红土,回到了我的家乡曲靖——阿诗玛传说生生不息的地方。江风拂过脸颊,我仿佛同时闻到了江水潮湿的气息和石林雨后红土特有的芬芳。两个地点,一个命运,这种时空交错带来的震撼,让我在那个夜晚清晰地听见了内心的旋律。我觉得,我必须写一首歌,从曲靖的土地出发,唱给这位再也没能回到故乡的女儿。

问:歌名中的“情话”,您认为具体指向什么?为何是“未说的”?
关兴瞳: 这“情话”的内涵,如同我们石林的岩层,是丰富的。最表层,是爱情。是电影里阿诗玛与阿黑被暴力中断的盟誓,更是现实中杨丽坤老师因病无法向丈夫唐凤楼完整倾诉的依赖与深情。唐先生用二十七年时光书写的无声守护,本身就是最动人的情话。
但更深层,这是一个漂泊灵魂对故土未能尽诉的乡愁。杨丽坤老师晚年心心念念的,不过是回一次云南,走走家乡的路。这份最简单质朴的渴望,成了她永远无法亲自说完的“情话”。我在歌里写“青石巷在暮色中摇”,那摇晃的,是每一个游子梦中故乡的模样。
同时,这也是我们这片土地对她的呼唤。石林不语,却记得每一个儿女。我们曲靖人心中,也始终为她留着一份未曾消散的惦念。这些,都是跨越时空的、未及言明的情话。
问:您如何将曲靖本土的彝族文化基因,与杨丽坤老师的个人命运相融合?
关兴瞳: 这首歌的魂魄,来自曲靖的山水与文化。比如“三步一跺脚踩碎月光”,直接源于我们彝族“跳月”、“打歌”的舞蹈韵律。杨丽坤老师从舞蹈演员起步,她的艺术之根,就扎在这样的节奏里。我写这句时,仿佛看见她年少时在练功房,或是在故乡月下起舞的身影,脚步坚定,银铃清脆。
再如“火塘烘烤陈年的诺言”。火塘,是彝家生活的中心,是温暖、传承与凝聚的象征。用它来隐喻唐凤楼先生给予妻子的、经年累月不离不弃的温暖,再恰当不过。而“荞麦地里生长出歌谣”,荞麦是这片高地上最顽强的生命,象征了阿诗玛传说的不朽,也象征了杨丽坤老师艺术生命那种在逆境中依然绽放的坚韧。
我使用了“赛啰赛”这样的彝语衬词。它不表具体词义,却是我们民歌呼吸的节奏,是情感最本真的流淌。我希望即使听不懂彝语的听众,也能感受到那股从红土地深处奔涌而出的、原始而浓烈的情感。

问:“月亮掉落在山崖”这句引起广泛共鸣,作为阿诗玛故乡的歌者,您如何理解这一意象?
关兴瞳: 在曲靖,尤其是雨后或月夜,你会看到雾气缭绕的石峰托着一轮明月,月亮仿佛就栖息在山崖之上,静谧而壮美。杨丽坤老师曾如一轮皓月,骤然升起,照亮了中国电影的银幕,其光华纯洁而耀眼。
然而,这轮明月不幸坠落。这不是自然的西沉,而是被突如其来的风暴卷入深渊,令人心碎。
但“掉落在山崖”不止于悲恸。在我们的文化认知中,生命终结亦是回归。月亮最终坠落在故乡的山崖,被嶙峋而坚实的岩石接住、拥抱。唐凤楼先生将她的部分骨灰送回云南,安葬于青山之中,便完成了这最终的“归根”。因此,这句词既有对个体命运多舛的深切叹惋,更有土地对女儿最终的接纳与永恒纪念。她化作了故乡山崖的一部分,从此,她的清辉与这片红土地上的月光永在。
问:通过这首歌,您希望完成怎样的表达与连接?
关兴瞳: 我希望这首歌能搭建一座桥。
一座连接传说与个人的桥。让听众知道,阿诗玛不只是一个神话人物,杨丽坤也不只是一个昔日明星。她们是一个具体、鲜活、承载了极致之美与深沉之痛的生命,她的根,深扎在我所生活的这片土地。
一座连接故乡与他乡的桥。杨丽坤老师从曲靖出发,归宿在上海。我希望这首歌能带着故乡的月光、山风与红土的气息,飘向那座她长眠的城市,完成一次迟来的、精神的“返乡”。
一座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桥。二十五年过去,时代变迁,但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不公命运的同情、对坚贞情感的敬仰,从未改变。这首歌是一次当代音乐人对历史伤痕的温柔抚摸,也是对永恒艺术价值的再度确认。
最后那不断重复、渐行渐远的呼唤,是我作为一个曲靖歌者,所能发出的最深沉的声音。呼唤那远行的女儿,也呼唤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份对美、对故土、对真挚情感的永恒眷恋。山风会传颂,红土会铭记。
此文内容为本网站刊发或转载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网无关。仅供读者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如有侵权、违规,可直接反馈本站,我们将会作删除处理,转转请注明出处:https://m.iv-field.com/8705.html